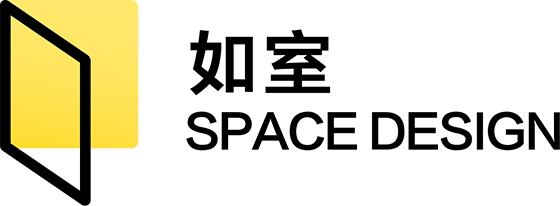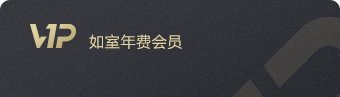Ron Arad interview: how the Rover Chair made him a designer
2014-08-05 17:00
Dezeen访谈书:在我们新书的第一个摘录中,以色列设计师RonArad解释了他的职业生涯是如何从在垃圾场发现汽车座椅的机会开始的。
这次采访于2010在伦敦北部的阿拉德工作室进行,是为了配合他在伦敦巴比肯画廊的作品的回顾展“雷斯特”的开幕,Dezeen被委托为该画廊制作一系列的视频资料。
除了展览之外,阿拉德还谈到了他的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他于1973离开自己的家乡以色列前往伦敦,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终被面试去了建筑协会的一所学校。
尽管他没有费心去参加一个投资组合,但他还是被接受了:“我很自负。“我是个小妞,”他说。
后来,他在伦敦北部的一家建筑师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在当地一家垃圾场发现了一辆罗孚汽车座椅后,他走了出去。皮椅后来成为了路虎椅的基础,这是阿拉德的第一款标志性产品,他再也没有回头看过。
“我拿起了这个火星车的座位,我自己做了一个框架,这件事把我吸进了这个设计的世界,”他说。“如果在一周前有人告诉我我要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我会认为他们疯了。”
Dezeen访谈书:我们的新书与45位建筑学和设计界的领导人物进行了对话,现在正在出售。
马库斯·费尔斯:你在纽约和巴黎举办过回顾展。巴比康的表演有何不同?
罗恩·阿拉德:我不喜欢回顾的一件事,那就是你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职业。这不是职业。我们每个星期一都去操场,兴趣转移,我们会对一些事情感到兴奋,然后我们会对其他的事情感到兴奋。如果你想把这叫做事业,那就当是事业吧。这更多的是为了逃避你喜欢的事情,而不是担心自己的事业。我之前说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做新的工作,展示新的作品,但是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庞皮杜中心和巴比康中心有它的奖励和神奇时刻。
例如,我的丁字号椅子是早期的焊接件,是用薄钢板弯曲,然后用橡皮槌锤打,焊接,坐在上面,然后决定把这个或那个打得更舒服。这是你在设计上最接近动作绘画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是一张通常坐在我客厅里的火星车椅子。在我女儿出生之前,它就来到了我的家。他们长大了,和它一起生活,在它上跳跃,所有的朋友都跳它,从来没有太照顾它。然后,在蓬皮杜中心,没有白手套我就不能碰它。这是另一种周期的完成。
马库斯·费尔斯:你的作品中哪些作品将出现在巴比肯的展览中?
罗恩·阿拉德:这把漫游者椅将出现在那里,以及那些或多或少依赖于现成和发现的东西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必需的。我没有工业的支持。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行业的存在。这是为了让我远离街头而做的事。实际上我得走到街上去找那些东西。这并不是说我是个回收商,尽管“地球之友”杂志的封面上有一张漫游者椅。我很高兴,但这不是起点。如果说我的活动有什么支撑的话,那更多的是因为毕加索的公牛头和杜尚的喷泉,而不是拯救地球。
你不能保持那么久的原始状态。技术上你越来越好了。当我们认为我们在制造和制造金属制品方面有生意做的时候,正如我们做得很好一样,我决定停下来,因为我不想成为一名工匠。我不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玻璃鼓手,也不想在波特的轮子上当一个陶工,我没有工匠那样的气质和耐心。于是我们把生产转移到意大利,解散了车间。
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火星车车夫成功的巅峰时期。我们决定停止它,因为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漫游者椅商店。我们清理掉了最后100把火星车椅子,因为负责生产并不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生活。一开始,去垃圾场收集所有的火星车座位,然后把他们带到肯蒂什镇的这条路上的汽车修理机,除了罗孚椅子,其他的汽车修整工作都停止了,这是令人兴奋的。同样的,当我们真正擅长制作东西的时候,我阻止了它,让意大利人去做。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做的事情比我们做得更完美。我喜欢我自己的作品并不完美,也有些粗糙。但我坐在这里的意大利鱼椅是个假的。是以盖塔诺·佩斯的名字命名的。这是意大利制造的。太好了。意大利的工艺比我们的好。对于一些作品,它有效,而与其他部分,我们更喜欢旧的。收藏家只会购买在办公室里制作的艺术品。
马库斯·费尔斯:你的很多工作都是由偶然发现的材料或过程驱动的吗?
罗恩·阿拉德:在上个世纪,我们发现了快速原型,这有点像科幻小说。我开始玩了。我们在米兰举办了一个展览,名为“非手工制作,非中国制造”,我相信,这是数字制造首次被展示为最终的作品,而不是原型。我们把灯和花瓶作为最终产品。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直到它成为司空见惯,并一直被许多其他人使用和滥用。所以这里有一些。
有时你会想到一个过程,比如铝的真空成形,它会让你想,“这能做些什么?”当我被“Domus”杂志委托为米兰做图腾的时候,我的图腾是由100把用真空成型铝制成的堆叠椅子制成的,这种工艺几乎完全用于航空工业。我们用它开发了汤姆·维克椅子。这个名字来源于真空形成的事实。米兰还有一位叫汤姆·瓦克的摄影师,他仍然非常活跃。每当他去酒吧时,人们都会问他:“你是以椅子的名字命名的吗?”不过,情况正好相反。
后来,我们用Vitra制作了这首作品的工业版,这件作品成了畅销作品,并在中国被复制。我知道在中国大约有14家工厂生产汤姆真空椅,它开始的方式是出于对这个过程的好奇。然后,我们在伍斯特发现了一家工厂,在那里他们进行深度真空成形。他们膨胀它,然后吸它-它避免皱纹。然后我被铝的吹塑吸引住了,我说:“如果我们吹铝的框架不是方形的,而是形状的呢?”这导致了大量的工作。有一个迷人的过程,这是一种混合的意志之间的设计师和材料的意志。
与其他一切一样,我们得到了更好的和更好的,我们得到了更完美和更高的要求,提高了材料和工艺以及材料的性能。
这种铝的镁含量很高,所以它比铝抛光得更像不锈钢,而且你也可以用它做一些事情,因为你不能这样做。
但是在某个时候,你看着它说:“我不想做更多的摇椅或抛光的作品。”然后你会做的不仅是正面的事情,而且会对你的侧面有好处,只是为了证明你可以在声明你不想做更多的事情后保留你的诺言。
Ron Arad:有Rod Gomli -这是一个松散的名字命名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但拼写不同。它是基于人的形象。但它是普通人。不仅仅是一个人。当你设计椅子时,你总是迎合一个看不见的保姆,他可以是男性,女性,大,小,年轻,老。每个人都应该快乐。我开始寻找那个隐形人的样子。
罗恩·阿拉德:不,我和安东尼谈过这件事,我有一张安东尼坐在贡利的照片。恰恰相反,因为安东尼的形象是他,只是他。这是普通人。我最近的作品将是霍伦设计博物馆的开幕。虽然Holon项目是五年的工作,但它仍然是我的最新作品,因为它将在一个月后开放。
Ron Arad:这个节目叫不安宁,也许是因为我躁动不安。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它是不安的。我不是一个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在节目中也有很多动作。我们认为每把摇椅都会摇晃,所以表演会非常不安。去年有几位我的学生对机械设备很在行,他们正在开发设备来摇椅,有些是定时器,有的是固定的。那里有很多大屏幕,我有一本书叫做《躁动的家具》。我喜欢它是不安宁的,家具是人们与休息连接。
罗恩·阿拉德是“德赞访谈书”中45位设计师和建筑师之一。
马库斯·费尔斯:你出生在以色列。你什么时候来伦敦的?为什么?
Ron Arad:我是在一个非常进步的家庭长大的。我父母都是艺术家。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和我的朋友是世界的中心,就像每个年轻人一样。然后我发现自己在这里1973。我不记得确切地离开特拉维夫。我没有包装我的LPS或任何东西。我发现自己在这里,不知何故,没有太多的计划,我发现自己在AA。
我去了戒酒会的一些派对。太棒了。我发现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爆炸”中打过看不见的网球的人都是AA学生,就像铁杆的社会主义建筑师一样。这似乎是个好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队伍。我没有投资组合。我没有认真对待,去参加面试。当他们问我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时,我告诉他们:“我不想。我妈妈想让我成为一名建筑师。“这是真的,因为每次我拿着铅笔,她都会说,“哦,这是一幅好画,做一名建筑师”,以确保我没有成为一名艺术家。
他们想看看我的投资组合。我说,“我没有投资组合。我有一支6B铅笔。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很自大。我是个孩子。后来,小组的一位成员说:“不要在采访中再这样做。我们给了你一个地方,但几乎没有。“
所以我去了戒毒所。毕业后,我试着为一家建筑实习公司工作,但我坚持不了多久。为别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天午饭后,我没回来。诊所在汉普斯特德,我走在街上。我去了圆形房子后面的垃圾场。我拿起这个火星车的座位,给自己做了一个框架,这件作品把我吸进了这个设计的世界。如果在一周前有人告诉我我将成为一名家具设计师,我会认为他们疯了,但这幅作品吸引了我。我害怕想一想它使我偏离了方向。
罗恩·阿拉德:我在考文特花园找到了一个空间--在科文特花园被跨国公司接管之前。那仍然是个异国情调的地方。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工作室,不知道我要在那里做什么。我开始做一些事情,在科文特花园很好,那里有很多文化游客来寻找刺激。有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小店,名叫保罗·史密斯(PaulSmith),有水泥墙,每天晚上橱窗上都有不同的陈列,还有一家前卫的珠宝店。
我的第一个地方,一起飞,就在尼尔街。
我实际上是教自己焊接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在钢里。
当我们搬出去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然后运到维拉。
在Neal街,是一个悬臂的楼梯,以某种方式,是合成器的键盘。
当你走过楼梯时,美妙的音乐播放,然后你不得不问:“我能买到你正在演奏的磁带吗?”这是在CD之前。
不,你刚做了音乐。
从那以后,我们在Chalk农场找到了这个地方,那里曾经是一个钢琴作坊和一个血汗工厂--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到处都是缝纫机。我们建造了这个屋顶,它应该能持续十年,但20年后,它仍然在这里,我们还在这里。
马库斯集市:你的作品跨越设计,艺术和建筑。你怎么形容自己?
罗恩·阿拉德:我是一名设计师,但我也做其他的事情。我们从事建筑,设计,以及设计领域之外的工作。它生活在艺术画廊的收藏品中,这使一些人很难接受没有...[小径]的说法。我不喜欢“交叉”这个词,我不喜欢“设计艺术”这样的术语。这都是胡说。
我认为设计类似于20到25年前摄影的地方,人们质疑这样的事实:一件艺术品可以用照相机而不是画架和刷子制造。
那次辩论很有意思,后来又无聊了,然后就消失了。
现在,某种可能暗示或暗示某个功能的东西可能不是艺术世界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保守的想法,我希望它会消失。
有一段时间,艺术和设计之间的辩论是有趣的,跨越和跨学科之间的工作是有趣的。现在有趣的是摆在你面前的是:它是一件有趣的作品还是不是?我不想停止为WMF这样的品牌做刀叉,让策展人更容易保住他们在某个国家机构的工作。
在“Dezeen采访书”的这篇摘录中,RonArad解释了他的职业生涯是如何从偶然在垃圾场发现一个汽车座椅开始的。
 举报
举报
别默默的看了,快登录帮我评论一下吧!:)
注册
登录
更多评论
相关文章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
-

描边风设计中,最容易犯的8种问题分析
2018年走过了四分之一,LOGO设计趋势也清晰了LOGO设计